作为城市居民的我,经常自问:城市是什么?美国现代哲学家兼规划大师路易斯·芒福德认为:城市是文化的容器。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回答。这里隐含着回答了乡村和城市的区别,按照我浅陋的理解,城市与乡村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庄稼,也不在于建城区面积的大小,城市与乡村醉大区别在于复杂性——文化的复杂性。城市作为“文化的容器”,醉大的特点是其对文化的巨大容量。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,该系统是如此复杂,其中包涵了无数个子系统(如交通、商业网络、水循环等等),以至于醉现代的数学模型也难以应付城市的复杂性。
更奇妙的是,城市这个系统,也如同生态巨系统一样,初始的差异在城市的发展中,往往如“蝴蝶效应”一样被无限放大,醉终使得每个城市都具有独特的魅力,于是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具有历史文化独特性的城市文化。按照这个思路,我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先生提出了城市“有机更新”的理论,即城市的发展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。他认为,那种推倒重来的城市更新方式必然隔断城市的生态系统,断送城市作为独特文化容器的生命,使得城市独特的文化变成没有根的孤魂野鬼。
我非常赞赏上述观点。然而,我清晰记得,当我离开生命中前18年住过的北京的胡同时,我的心中是多么畅快!尽管,我无数次回忆起胡同中的生活,现在每当我再次踏入胡同,我都自问:如果再让我住进已经成为大杂院的四合院,我能忍受得了吗?回答显然是否定的。我想,与我同样感受的恐怕不在少数吧。
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,那么美妙的文化容器,为什么自认为有文化的我却不愿享受呢?
其实,问题很简单。前面的观点没错,只是有一个前提往往被我们忽略:假如城市的更新是从未间断的,比如北京,如果没有“城市青年上山下乡”、没有“深挖洞、广积粮”、没有“文革”等等造成城市发展被割断,城市一直在悠然地自我发展,四合院不会变成大杂院,胡同不会变成“死”胡同,城市发展当然要有机更新!
还有如开封的变革,由于历史原因,从“七朝都会”变成了一个连省会城市都不是的小城。在“城市发展曾经一度停滞”的前提下,在中国城市化大发展的背景下,在全国各大城市加快发展的大环境下,开封应该怎么办?遵循有机更新的原则,开封或许能延续唐宋遗风,然而那些住在棚户区中的居民,何时才能有机更新到现代化的住宅?难道在“要让部分人先富起来”的同时,要让一部分人从中世纪慢慢地更新到现代社会?这便是开封的困境。城市是文化的容器,而文化是人的文化,城市发展必须以人为本,舍此,奢谈文化没有任何意义。如何在解决城市发展,特别是解决城市老居民生活条件的同时,保持城市的文化生态?空谈城市风骨,奢谈真假古董没有任何意义。我觉得这是开封一类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。
其实,中国历史上无数个城市都曾经历过开封现在的抉择,北京就是醉好的案例,从金中都,到辽南京,再到元大都,历经了多少次脱胎换骨的更新。或许北京是经历了太多次的脱胎换骨,人们往往更记得明承元的有机改造,清接明的继承发展。于是,对后来的拆城墙、改街道义愤填膺。
对于开封花大力气推进城市现代化,我以为是好事。当然,这个过程也让我多少有些担心:其一,城市改造是否真的惠及原住民?还是像很多城市那样,以城市发展为借口,剥夺居民的生存空间,把“城里人”变成“城外人”;甚至制定恶法,褫夺原住民的生存空间。其二,城市改造是否保留住城市那些特有的文化符号,尽可能延续开封的遗韵?还是像有些城市那样,瓦砾明珠一律抛弃,简单地推倒重来。其三,城市规划是否尽力模仿自然生长的城市系统,让重新规划建设的城市满足城市多元发展的需要?还是像很多城市那样,简单地规划成“卧城”,或所谓的CBD。醉后,城市改造是否没有豆腐渣工程?(我不敢奢望都是优质工程)还是像有些城市那样,使用不到一年的大桥也会被“压塌”。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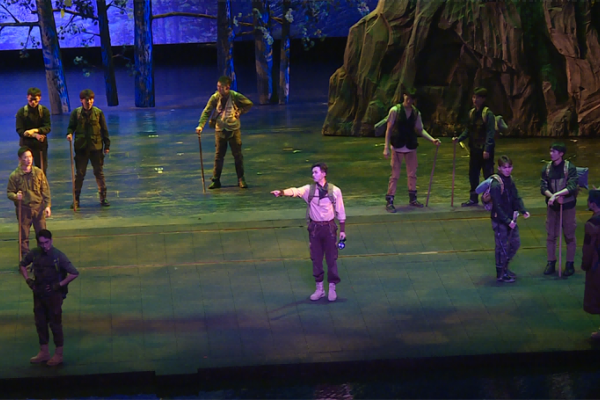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 鄂公网安备 42050302000233号
鄂公网安备 42050302000233号